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恩格斯(寫於1886年)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1995年版,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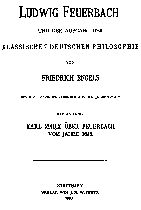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恩格斯(寫於1886年)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1995年版,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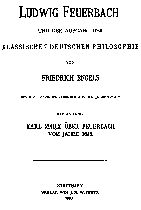
|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說,1845年我們兩人在布魯塞爾著手“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主要由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后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后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愿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們兩人誰也沒有過机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關於我們和黑格爾的關系,我們曾經在一些地方作了說明,但是無論哪個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統的。至於費爾巴哈,雖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中間環節,我們卻從來沒有回顧過他。
這期間,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語言中都找到了擁護者。另一方面,德國的古典哲學在國外,特別是在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有某種复活。甚至在德國,各大學裡借哲學名義來施舍的折衷主義殘羹剩汁,看來已叫人吃厭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感到越來越有必要把我們同黑格爾哲學的關系,我們怎樣從這一哲學出發又怎樣同它脫离,作一個簡要而又系統的闡述。同樣,我也感到我們還要還一筆信譽債,就是要完全承認,在我們的狂風暴雨時期,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比黑格爾以後任何其他哲學家都大。所以,當《新時代》雜志編輯部要我寫一篇批評文章來評述施達克那本論費爾巴哈的書時,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這篇文章發表在該雜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現在經過修訂以單行本出版。
在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部分是閘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衹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麼不夠。舊稿中缺少對費爾巴哈學說本身的批判﹔所以,舊稿對現在這一目的是不適用的。可是我在馬克思的一本舊筆記中找到了十一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現在作為本書附錄刊印出來。這是匆匆寫成的供以後研究用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於倫敦
--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88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
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1]使我們返回到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就時間來說离我們不過一代之久,但是它對德國現在的一代人卻如此陌生,似乎已經整整一個世紀了。然而這終究是德國准備1848年革命的時期﹔那以后我國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1848年的繼續,僅僅是革命遺囑的執行罷了。
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一樣,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潰的前導。但是這兩個哲學革命看起來是多麼不同啊!法國人同整個官方科學,同教會,常常也同國家進行公開的鬥爭﹔他們的著作在國外,在荷蘭或英國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隨時都可能進巴士底獄。相反,德國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國家任命的青年的導師,他們的著作是公認的教科書,而全部發展的最終体系,即黑格爾的体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推崇為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哲學!在這些教授后面,在他們的迂腐晦澀的言詞后面,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語句裡面竟能隱藏著革命嗎?那時被認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對這種使頭腦混亂的哲學嗎?但是,不論政府或自由派都沒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個人在1833年已經看到了,這個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舉個例子來說吧。不論哪一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一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一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
所以,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某種稅制”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衹是意味著:這個國家衹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极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裡,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証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
但是,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裡衹限於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一堆現成的、一經發現就衹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現在,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在哲學認識的領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認識領域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也是如此。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衹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衹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和世界市場在實踐中推甸了一切穩固的、歷來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樣,這種辯証哲學推甸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一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証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
我們在這裡用不著去研究這種觀察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學的現狀完全符合的問題,自然科學預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適合居住狀況的相當肯定的末日,從而承認,人類歷史不僅有上升的過程,而且有下降的過程。無論如何,我們离社會歷史開始下降的轉折點還相當遙遠,我們也不能要求黑格爾哲學去研究當時還根本沒有被自然科學提到日程上來的問題。
但是這裡確實必須指出一點:黑格爾并沒有這樣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闡述。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但是他本人從來沒有這樣明确地作出這個結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個体系,而按照傳統的要求,哲學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所以,黑格爾,特別是在《邏輯學》中,盡管如此強調這種永恆真理不過是邏輯的或歷史的過程本身,他還是覺得自己不得不給這個過程一個終點,因為他總得在某個地方結束他的体系。在《邏輯學》中,他可以再把這個終點作為起點,因為在這裡,終點即絕對觀念──它所以是絕對的,衹是因為他關於這個觀念絕對說不出什麼來──“外化”也就是轉化為自然界,然後在精神中,即在思維中和在歷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學的終點上這樣返回到起點,衹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把歷史的終點設想成人類達到對這個絕對觀念的認識,并宣布對絕對觀念的這種認識已經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達到了。但是這樣一來,黑格爾体系的全部教條內容就被宣布為絕對真理,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條東西的辯証方法是矛盾的﹔這樣一來,革命的方面就被過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學的認識上是這樣,在歷史的實踐上也是這樣。人類既然通過黑格爾這個人想出了絕對觀念,那麼在實踐上也一定達到了能夠在現實中實現這個絕對觀念的地步。因此,絕對觀念對同時代人的實踐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太高。因此,我們在《法哲學》的結尾發現,絕對觀念應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許諾而又不予兌現的那種等級君主制中得到實現,就是說,應當在有產階級那種适應於當時德國小資產階級關系的、有限的和溫和的間接統治中得到實現﹔在這裡還用思辨的方法向我們論証了貴族的必要性。
可見,單是體系的內部需要就足以說明,為什麼徹底革命的思維方法竟產生了極其溫和的政治結論。這個結論的特殊形式當然是由下列情況造成的: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而且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一樣,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歌德和黑格爾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是奧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擺脫德國庸人的習氣。
但是,這一切并沒有妨礙黑格爾的體系包括了以前任何體系所不可比擬的廣大領域,而且沒有妨礙它在這一領域中闡發了現在還令人驚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現象學(也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學和精神古生物學類似的學問,是對個人意識各個發展階段的闡述,這些階段可以看作人類意識在歷史上所經過的各個階段的縮影)、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而精神哲學又分成各個歷史部門來研究,如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哲學史、美學等等,──在所有這些不同的歷史領域中,黑格爾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貫穿這些領域的發展線索﹔同時,因為他不僅是一個富於創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識淵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個領域中都起了划時代的作用。當然,由於“体系”的需要,他在這裡常常不得不求救於強制性的結构,對這些結构,直到現在他的渺小的敵人還發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這些結构僅僅是他的建築物的骨架和腳手架﹔人們衹要不是無謂地停留在它們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廈裡面去,那就會發現無數的珍寶,這些珍寶就是在今天也還保持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學家那裡,正是“體系”是暫時性的東西,這恰恰因為“體系”產生於人類精神的永恆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遠消除了,那麼我們就達到了所謂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就完結了,而世界歷史雖然已經無事可做,卻一定要繼續發展下去──因而這是一個新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一旦我們認識到(就獲得這種認識來說,歸根到底沒有一個人比黑格爾本人對我們的幫助更大),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完成那衹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麼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一邊,而沿著實証科學和利用辯証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總之,哲學在黑格爾那裡完成了,一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一方面,因為他(雖然是不自覺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走出這些体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爾的體系在德國的富有哲學味道的氣氛中曾發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這是一次勝利進軍,它延續了几十年,而且決沒有隨著黑格爾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從1830年到1840年,“黑格爾主義”取得了獨占的統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敵手﹔正是在這個時期,黑格爾的觀點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大量滲入了各種科學,也滲透了通俗讀物和日報,而普通的“有教養的意識”就是從這些通俗讀物和日報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這一全線胜利僅僅是一種內部鬥爭的序幕罷了。
黑格爾的整個學說,如我們所看到的,為容納各種极不相同的實踐的党派觀點留下了廣闊場所﹔而在當時的理論的德國,有實踐意義的首先是兩種東西:宗教和政治。特別重視黑格爾的体系的人,在兩個領域中都可能是相當保守的﹔認為辯証方法是主要的東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屬於最极端的反對派。黑格爾本人,雖然在他的著作中相當頻繁地爆發出革命的瞄火,但是總的說來似乎更傾向於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費的“艱苦的思維勞動”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費的要多得多。到30年代末,他的學派內的分裂越來越明顯了。左翼,即所謂青年黑格爾派,在反對虔誠派的正統教徒和封建反動派的斗爭中一點一點地放棄了在哲學上對當前的緊迫問題所采取的超然態度,由於這種態度,他們的學說在此之前曾經得到國家的容忍、甚至保護﹔到了1840年,正統教派的虔誠和封建專制的反動隨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這時人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公開站在這一派或那一派方面了。斗爭依舊是用哲學的武器進行的,但已經不再是為了抽象的哲學目的﹔問題已經直接是要消滅傳統的宗教和現存的國家了。如果說在《德國年鑑》中實踐的最終目的主要還是穿著哲學的外衣出場,那麼,在1842年的《萊茵報》上青年黑格爾學派已經直接作為努力向上的激進資產階級的哲學出現,衹是為了迷惑書報檢查机關才用哲學偽裝起來。
但是,政治在當時是一個荊棘叢生的領域,所以主要的斗爭就轉為反宗教的斗爭﹔這一斗爭,特別是從1840年起,間接地也是政治斗爭。1835年出版的施特勞斯的《耶穌傳》成了第一個推動力。后來,布魯諾.鮑威爾反對該書中所闡述的福音神話發生說,証明許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虛构的。兩人之間的爭論是在“自我意識”對“實体”的斗爭這一哲學幌子下進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團体內部通過不自覺的、傳統的創作神話的途徑形成的呢,還是福音書作者自己虛构的,──這個問題竟擴展為這樣一個問題:在世界歷史中起決定作用的力量是“實体”呢,還是“自我意識”﹔最后,出現了施蒂納,現代無政府主義的先知(巴枯宁從他那裡抄襲了許多東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壓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識”。
我們不打算更詳細地考察黑格爾學派解体過程的這一方面。在我們看來,更重要的是:對現存宗教進行斗爭的實踐需要,把大批最堅決的青年黑格爾分子推回到英國和法國的唯物主義。他們在這裡跟自己的學派的体系發生了沖突。唯物主義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現實的東西,而在黑格爾的体系中自然界衹是絕對觀念的“外化”,可以說是這個觀念的下降﹔無論如何,思維及其思想產物即觀念在這裡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衹是由於觀念的下降才存在。他們就在這個矛盾中彷徨,盡管程度各不相同。
這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出版了。它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這就一下子消除了這個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賴任何哲學而存在的﹔它是我們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產物)賴以生長的基礎﹔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造出來的那些最高存在物衹是我們自己的本質的虛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開并被拋在一旁了,矛盾既然僅僅是存在於想象之中,也就解決了。──這部書的解放作用,衹有親身体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驗這種新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盡管還有種種批判性的保留意見),這可以從《神圣家族》中看出來。
甚至這部書的缺點也加強了它的一時的影響。美文學的、有時甚至是夸張的筆調贏得了廣大的讀者,無論如何,在抽象而費解的黑格爾主義的長期統治以后,使人們的耳目為之一新。對於愛的過度崇拜也是這樣。這種崇拜,盡管不能認為有道理,在“純粹思維”的已經變得不能容忍的至高統治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從1844年起在德國的“有教養的”人們中間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正是同費爾巴哈的這兩個弱點緊密相連的。它以美文學的詞句代替了科學的認識,主張靠“愛”來實現人類的解放,而不主張用經濟上改革生產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一句話,它沉溺在令人厭惡的美文學和泛愛的空談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爾﹒格律恩先生。
還有一點不應當忘記:黑格爾學派雖然解体了,但是黑格爾哲學并沒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各自抓住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方面,在論戰中互相攻擊。費爾巴哈打破了黑格爾的体系,簡單地把它拋在一旁。但是簡單地宣布一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辦法來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下面可以看到,這一任務是怎樣實現的。
但是這時,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氣地把全部哲學都撇在一旁,正如費爾巴哈把他的黑格爾撇在一旁一樣。這樣一來,費爾巴哈本人也被擠到後台去了。
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在遠古時代,人們還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構造,并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2],於是就產生一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体的活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寓於這個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离開身体的靈魂的活動。從這個時候起,人們不得不思考這種靈魂對外部世界的關系。如果靈魂在人死時离開肉体而繼續活著,那就沒有理由去設想它本身還會死亡﹔這樣就產生了靈魂不死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那個發展階段出現決不是一種安慰,而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并且往往是一種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裡就是這樣。關於個人不死的無聊臆想之所以普遍產生,不是因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為人們在普遍愚昧的情況下不知道對已經被認為存在的靈魂在肉体死后該怎麼辦。由於十分相似的原因,通過自然力的人格化,產生了最初的神。隨著各種宗教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神越來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過智力發展中自然發生的抽象化過程──几乎可以說是蒸餾過程,在人們的頭腦中,從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許多神中產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觀念。
因此,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像一切宗教一樣,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的愚昧無知的觀念。但是,這個問題,衹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思維對存在的地位問題,這個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也起過巨大作用的問題:什麼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著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
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承認某種創世說的人(而創世說在哲學家那裡,例如在黑格爾那裡,往往比在基督教那裡還要繁雜和荒唐得多),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裡也不是在別的意義上使用的。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給它們加上別的意義,就會造成怎樣的混亂。
但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系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作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爾那裡,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認識的,正是這個世界的思想內容,也就是那種使世界成為絕對觀念的逐步實現的東西,這個絕對觀念是從來就存在的,是不依賴於世界并且先於世界而在某處存在的﹔但是思維能夠認識那一開始就已經是思想內容的內容,這是十分明顯的。同樣明顯的是,在這裡,要証明的東西已經默默地包含在前提裡面了。但是,這決不妨□黑格爾從他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論証中作出進一步的結論:他的哲學因為對他的思維來說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証實,人類就要馬上把他的哲學從理論轉移到實踐中去,并按照黑格爾的原則來改造整個世界。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學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哲學家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認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學家中,休謨和康德就屬於這一類,而他們在哲學的發展上是起過很重要的作用的。對駁斥這一觀點具有決定性的東西,凡是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所能說的,黑格爾都已經說了﹔費爾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義的東西,與其說是深刻的,不如說是机智的。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自己能夠制造出某一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生產出來,并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証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麼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動植物体內所產生的化學物質,在有机化學開始把它們一一制造出來以前,一直是這種“自在之物”﹔一旦把它們制造出來,“自在之物”就變成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們已經不再從地裡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簡單得多的方法從煤焦油裡提煉出來了。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有年之久一直是一種假說,這個假說盡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畢竟是一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說所提供的數据,不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后來加勒确實發現了這個行星的時候,哥白尼的學說就被証實了。如果新康德主義者企圖在德國复活康德的觀點,而不可知論者企圖在英國复活休謨的觀點(在那裡休謨的觀點從來沒有絕跡),那麼,鑑於這兩種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早已被駁倒,這種企圖在科學上就是開倒車,而在實踐上衹是一種暗中接受唯物主義而當眾又加以拒絕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從笛卡兒到黑格爾和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這一長時期內,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衹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在唯物主義者那裡,這已經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義体系也越來越加進了唯物主義的內容,力圖用泛神論來調和精神和物質的對立﹔因此,歸根到底,黑格爾的体系衹是一種就方法和內容來說唯心主義地倒置過來的唯物主義。
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施達克在他對費爾巴哈的評述中,首先研究費爾巴哈對思維和存在的關系這個基本問題的立場。在簡短的導言裡,作者對以前的、特別是從康德以來的哲學家的見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澀難懂的哲學語言來闡述的,并且由於過分形式主義地拘泥於黑格爾著作中的個別詞句而大大貶低了黑格爾。在這個導言以后,他詳細地敘述了費爾巴哈的有關著作中相繼表現出來的這位哲學家的“形而上學”本身的發展進程。這一部分敘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過像整本書一樣,哲學用語堆砌得太多,而這決不是到處都不可避免的。作者越是不保持同一學派或者哪怕是費爾巴哈本人的用語,越是把各種流派、特別是現在流行的自封的哲學派別的用語混在一起,這種堆砌所造成的混亂就越大。
費爾巴哈的發展進程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誠然,他從來不是完全正統的黑格爾主義者)走向唯物主義的發展進程,這一發展使他在一定階段上同自己的這位先驅者的唯心主義体系完全決裂了。他勢所必然地終於認識到,黑格爾的“絕對觀念”之先於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邏輯範疇的預先存在”,不外是對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虛幻殘余﹔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現實的﹔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不論它看起來是多麼超感覺的,總是物質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腦的產物。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而精神本身衹是物質的最高產物。這自然是純粹的唯物主義。但是費爾巴哈到這裡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學偏見,即不反對事情本身而反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的偏見。他說:
“在我看來,唯物主義是人的本質和人類知識的大廈的基礎﹔但是,我認為它不是生理學家、狹義的自然科學家如摩萊肖特所認為的而且從他們的觀點和專業出發所必然認為的那種東西,即大廈本身。向後退時,我同唯物主義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進時就不一致了。”
費爾巴哈在這裡把唯物主義這種建立在對物質和精神關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觀同這一世界觀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即世紀所表現的特殊形式混為一談了。不僅如此,他還把唯物主義同它的一種膚淺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為一談,18世紀的唯物主義現在就以這種形式繼續存在於自然科學家和醫生的頭腦中,并且被畢希納、福格特和摩萊肖特在50年代拿著到處叫賣。但是,像唯心主義一樣,唯物主義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甚至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划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得到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後,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裡開辟出來了。
上一世紀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机械唯物主義,因為那時在所有自然科學中衹有力學,而且衹有固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學,簡言之,即重力的力學,達到了某種完善的地步。化學剛剛處於幼稚的燃素說的形態中。生物學尚在襁褓中﹔對植物和動物的机体衹作過粗淺的研究,并用純粹机械的原因來解釋﹔正如在笛卡兒看來動物是机器一樣,在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是机器。僅僅運用力學的尺度來衡量化學性質的和有机性質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力學定律雖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較高的定律排擠到次要地位),這是法國古典唯物主義的一個特有的、但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這種唯物主義的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在於: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同當時的自然科學狀況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証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适應的。人們已經知道,自然界處在永恆的運動中。但是根据當時的想法,這種運動是永遠繞著一個圓圈旋轉,因而始終不會前進﹔它總是產生同一結果。這種想法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陽系發生說剛剛提出,而且還衹是被看作純粹的奇談。地球發展史,即地質學,還完全沒有人知道,而關於現今的生物是由簡單到复雜的長期發展過程的結果的看法,當時還根本不可能科學地提出來。因此,對自然界的非歷史觀點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這一點大可不必去責備18世紀的哲學家,因為連黑格爾也有這種觀點。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衹是觀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時間上發展,衹能在空間擴展自己的多樣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發展階段同時地、并列地展示出來,并且注定永遠重复始終是同一的過程。黑格爾把發展是在空間以內、但在時間(這是一切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外發生的這種謬論強加於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質學、胚胎學、植物和動物生理學以及有机化學都已經建立起來,并且在這些新科學的基礎上到處都出現了對後來的進化論的天才預想(例如歌德和鵑馬克)的時候。但是,体系要求這樣,於是,方法為了驗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這種非歷史觀點也表現在歷史領域中。在這裡,反對中世紀殘余的斗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蠻狀態造成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裡一個挨著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紀的巨大的技朮進步,這一切都沒有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証和插圖的匯集罷了。
50年代在德國把唯物主義庸俗化并到處兜售的小販們,絲毫沒有越出他們的老師們的這個範圍。自然科學後來獲得的一切進步,僅僅成了他們否認有世界創造主存在的新論据﹔而進一步發展理論,實際上他們根本不去做。如果說唯心主義當時已經智窮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那麼,它感到滿足的是,唯物主義在這個時候更是婚河日下。費爾巴哈拒絕為這種唯物主義負責是完全對的﹔衹是他不應該把這些巡回傳教士的學說同一般唯物主義混淆起來。
但是,這裡應當注意兩種情況。第一,費爾巴哈在世時,自然科學也還處在劇烈的醞釀過程中,這一過程衹是在最近15年才達到了足以澄清問題的相對完成的地步﹔新的認識材料以空前的規模被提供出來,但是,衹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紛紛涌來的這一大堆雜亂的發現中建立起聯系,從而使它們有了條理。雖然這三個決定性的發現──細胞、能量轉化和以達爾文命名的進化論的發現,費爾巴哈在世時全看到了,但是,這位在鄉間過著孤寂生活的哲學家怎麼能夠對科學充分關注,給這些發現以足夠的評价呢?何況對這些發現就連當時的自然科學家有的還持有异原,有的還不懂得充分利用。這裡衹能歸咎於德國的可怜狀況,由於這種狀況,當時哲學講座全被那些故弄玄虛的折衷主義的小識小見之徒所占据,而比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費爾巴哈,卻不得不在窮鄉僻壤中過著農民式的孤陋寡聞的生活。因而,現在已經成為可能的、排除了法國唯物主義的一切片面性的、歷史的自然觀,始終沒有為費爾巴哈所了解,這就不是他的過錯了。
第二,費爾巴哈說得完全正确:純粹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雖然
“是人類知識的大廈的基礎,但不是大廈本身”。
這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問題在於使關於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并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但是,這一點費爾巴哈是做不到的。他雖然有“基礎”,但是在這裡仍然受到傳統的唯心主義的束縛,這一點他自己也是承認的,他說:
“向後退時,我同唯物主義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進時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這裡,在社會領域內,正是費爾巴哈本人沒有“前進”,沒有超過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觀點,這仍舊主要是由於他的孤寂生活,這種生活迫使這位比其他任何哲學家都更愛好社交的哲學家從他的孤寂的頭腦中,而不是從同與他才智相當的人們的友好或敵對的接触中產生出自己的思想。費爾巴哈在這個領域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義者,我們將在下面加以詳細的考察。這裡還應當指出,施達克在找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時找錯了地方。他說:
“費爾巴哈是唯心主義者,他相信人類的進步。”(第19頁)“唯心主義仍舊是一切的基礎,根基。在我們看來,實在論衹是在我們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圖時使我們不致誤入迷途而已。難道同情、愛以及對真理和正義的熱誠不是理想的力量嗎?”(第VⅢ頁)
第一,在這裡無非是把對理想目的的追求叫作唯心主義。但這些目的至多同康德的唯心主義及其“絕對命令”有必然聯系﹔然而康德自己把他的哲學叫作“先驗的唯心主義”,決不是因為那裡也講到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於別的理由,這是施達克會記得的。有一種迷信,認為哲學唯心主義的中心就是對道德理想即對社會理想的信仰,這種迷信是在哲學之外產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詩歌中符合他們需要的少數哲學上的衹言片語背得爛熟的德國庸人中產生的。沒有一個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義者黑格爾更尖銳地批評了康德的軟弱無力的“絕對命令”(它之所以軟弱無力,是因為它要求不可能的東西,因而永遠達不到任何現實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傳播的那種沉湎於不能實現的理想的庸人習气(見《現象學》)。
第二,決不能避免這種情況: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甚至吃喝也是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饑渴而開始,并且同樣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飽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机、意志,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并且以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個人衹是由於他追求“理想的意圖”并承認“理想的力量”對他的影響,就成了唯心主義者,那麼任何一個發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義者了,怎麼還會有唯物主義者呢?
第三,關於人類(至少在現時)總的說來是沿著進步方向運動的這種信念,是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絕對不相干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同自然神論者伏爾泰和盧梭一樣,几乎狂熱地抱有這種信念,并且往往為它付出最大的個人犧牲。如果說有誰為了“對真理和正義的熱誠”(就這句話的正面的意思說)而獻出了整個生命,那麼,例如狄德羅就是這樣的人。由此可見,施達克把這一切說成是唯心主義,這衹是証明: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以及兩個派別的全部對立,在這裡對他來說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
事實上,施達克在這裡向那種由於教士的多年誹謗而流傳下來的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的庸人偏見作了不可饒恕的讓步,雖然這也許是不自覺的。庸人把唯物主義理解為貪吃、酗酒、娛目、肉欲、虛榮、愛財、吝嗇、貪婪、牟利、投机,簡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戀著的一切齷齪行為﹔而把唯心主義理解為對美德、普遍的人類愛的信仰,總之,對“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別人面前夸耀這個“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衹是在這樣的時候才相信這個“美好世界”,這時,他由於自己習以為常的“唯物主義的”放縱而必然感到懊喪或遭到破產,并因此唱出了他心愛的歌:人是什麼?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達克極力保護費爾巴哈,反對現今在德國以哲學家名義大吹大擂的大學教師們的攻擊和學說。對關心德國古典哲學的這些不肖子孫的人們來說,這的确是很重要的﹔對施達克本人來說,這也許是必要的。不過我們就怜惜怜惜讀者吧。
我們一接觸到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他的真正的唯心主義就顯露出來了。費爾巴哈決不希望廢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學本身應當融化在宗教中。
“人類的各個時期僅僅由於宗教的變遷而彼此區別開來。某一歷史運動,衹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時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應當說宗教也存在於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質。”(引自施達克的書,第168頁)
按照費爾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的關系、心靈的關系,過去這種關系是在現實的虛幻映象中(借助於一個神或許多神,即人類特性的虛幻映象)尋找自己的真理,現在卻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在我和妳之間的愛中尋找自己的真理了。歸根到底,在費爾巴哈那裡,性愛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實現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與人之間的、特別是兩性之間的感情關系,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而性愛在最近800年間獲得了這樣的發展和地位,竟成了這個時期中一切詩歌必須環繞著旋轉的軸心了。現存的通行的宗教衹限於使國家對性愛的管理即婚姻立法神圣化﹔這些宗教也許明天就會完全消失,但是愛情和友誼的實踐并不會發生絲毫變化。在法國,從1793年到1798年,基督教的确曾經消失到這種程度,連拿破侖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難,但是在這一期間,并沒有感覺到需要用費爾巴哈意義上的宗教去代替它。
在這裡,費爾巴哈的唯心主義就在於:他不是拋開對某種在他看來也已成為過去的特殊宗教的回憶,直截了當地按照本來面貌看待人們彼此間以相互傾慕為基礎的關系,即性愛、友誼、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斷言這些關系衹有在用宗教名義使之神圣化以後才會獲得自己的完整的意義。在他看來,主要的并不是存在著這種純粹人的關系,而是要把這些關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這些關系衹是在蓋上了宗教的印記以後才被認為是完滿的。宗教一詞是從religare一詞來的,本來是聯系的意思。因此,兩個人之間的任何聯系都是宗教。這種詞源學上的把戲是唯心主義哲學的最後一著。這個詞的意義,不是按照它的實際使用的歷史發展來決定,而竟然按照來源來決定。因此,僅僅為了使宗教這個對唯心主義回憶很寶貴的名詞不致從語言中消失,性愛和性關系竟被尊崇為“宗教”。在40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義者正是這樣說的,他們也認為不信宗教的人衹是一種怪物,并且對我們說:因此,無神論就是妳們的宗教!費爾巴哈想以一種本質上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為基礎建立真正的宗教,這就等於把現代化學當作真正的煉金朮。如果無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麼沒有哲人之石的煉金朮也可以存在了。況且,煉金術和宗教之間是有很緊密的聯系的。哲人之石有許多類似神的特性,公元頭兩世紀埃及和希腊的煉金術士在基督教學說的形成上也出了一份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証明了這一點。
費爾巴哈的下面這個論斷是絕對錯誤的:
“人類的各個時期僅僅由於宗教的變遷而彼此區別開來。”
重大的歷史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衹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種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言。古老的自發產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傳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獨立遭到破壞,它們便失掉任何抵抗力﹔拿日耳曼人來說,甚至他們一接触正在崩潰的羅馬世界帝國以及它剛剛采用的、适應於它的經濟、政治、精神狀態的世界基督教,這種情形就發生了。僅僅在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裡,我們才發現比較一般的歷史運動帶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在基督教傳播的範圍內,具有真正普遍意義的革命也衹有在資產階級解放斗爭的最初階段即從13世紀到17世紀,才帶有這種宗教色彩﹔而且,這種色彩不能像費爾巴哈所想的那樣,用人的心靈和人的宗教需要來解釋,而要用以往的整個中世紀的歷史來解釋,中世紀的歷史衹知道一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但是到了18世紀,資產階級已經強大得足以建立他們自己的、同他們的階級地位相适應的意識形態了,這時他們才進行了他們的偉大而徹底的革命──法國革命,而且僅僅訴諸法律的和政治的觀念,衹是在宗教擋住他們的道路時,他們才理會宗教﹔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要用某種新的宗教來代替舊的宗教﹔大家知道,羅伯斯比爾在這方面曾遭受了怎樣的失敗。
同他人交往時表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經被我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以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社會破壞得差不多了。我們沒有理由把這種感情尊崇為宗教,從而更多地破壞這種可能性。同樣,對歷史上的重大的階級斗爭的理解,特別是在德國,已經被流行的歷史編纂學弄得夠模糊了,用不著我們去把這些斗爭的歷史變為教會史的單純附屬品,使這種理解成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經离開費爾巴哈多麼遠了。他那贊美新的愛的宗教的“最美麗的篇章”現在已經不值一讀了。
費爾巴哈認真地研究過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即以一神教為基礎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衹是人的虛幻的反映、映象。但是,這個神本身是長期的抽象過程的產物,是以前的許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來的精華。與此相應,被反映為這個神的人也不是一個現實的人,而同樣是許多現實的人的精華,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個思想上的形象。費爾巴哈在每一頁上都宣揚感性,宣揚專心研究具体的東西、研究現實,可是這同一個費爾巴哈,一談到人們之間純粹的性關系以外的某種關系,就變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這種關系中僅僅看到一個方面──道德。在這裡,同黑格爾比較起來,費爾巴哈的惊人的貧乏又使我們詫异。黑格爾的倫理學或關於倫理的學說就是法哲學,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倫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會、國家。在這裡,形式是唯心主義的,內容是實在論的。法、經濟、政治的全部領域連同道德都包括進去了。在費爾巴哈那裡情況恰恰相反。就形式講,他是實在論的,他把人作為出發點﹔但是,關於這個人生活的世界卻根本沒有講到,因而這個人始終是在宗教哲學中出現的那種抽象的人。這個人不是從娘胎裡生出來的,他是從一神教的神羽化而來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現實的、歷史地發生和歷史地确定了的世界裡面﹔雖然他同其他的人來往,但是任何一個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樣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學裡,我們終究還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倫理學裡,連這最後一點差別也消失了。的确,在費爾巴哈那裡間或也出現這樣的命題:
“皇宮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妳因為饑餓、貧困而身体內沒有養料,那麼妳的頭腦中、妳的感覺中以及妳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用的養料了。”──“政治應當成為我們的宗教”,等等。
但是,費爾巴哈完全不知道用這些命題去干什麼,它們始終是純粹的空話,甚至施達克也不得不承認,政治對費爾巴哈是一個不可通過的區域,而
“關於社會的學說,即社會學,對他來說,是一個未知的領域”。
在善惡對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爾比起來也是膚淺的。黑格爾指出:
“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裡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証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歷史對他來說是一個不愉快的可怕的領域。他有句名言:
“當人最初從自然界產生的時候,他也衹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歷史的產物。”──
甚至這句名言在他那裡也是根本不結果實的。
從上述一切可以明白,關於道德,費爾巴哈所告訴我們的東西衹能是极其貧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來就有的,因而應當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雙重的矯正。第一,受到我們的行為的自然後果的矯正:酒醉之後,必定頭痛﹔放蕩成習,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們的行為的社會後果的矯正:要是我們不尊重他人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麼他們就會反抗,妨礙我們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見,我們要滿足我們的這種欲望,就必須能夠正确地估量我們的行為的後果,另一方面還必須承認他人有相應的欲望的平等權利。因此,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又是愛!),這就是費爾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則,其他一切准則都是從中引伸出來的。無論費爾巴哈的妙語橫生的原論或施達克的熱烈無比的贊美,都不能掩蓋這几個命題的貧乏和空泛。
如果一個人衹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衹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滿足,而且決不會對己對人都有利。他的這種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滿足的手段:食物、异性、書籍、娛樂、辯論、活動、消費和加工的對象。費爾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個人無疑地都有這些滿足欲望的手段和對象為前提,或者衹向每一個人提供無法應用的忠告,因而對於沒有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這一點,費爾巴哈自己也說得很直截了當:
“皇宮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妳因為饑餓、貧困而身体內沒有養料,那麼妳的頭腦中、妳的感覺中以及妳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用的養料了。”
至於說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情況是否好一些呢?費爾巴哈提出這種要求,認為這種要求是絕對的,是适合於任何時代和任何情況的。但是這種要求從什麼時候起被認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在中世紀的農奴和領主之間,難道談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嗎?被壓迫階級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無情地“依法”變成了統治階級的這種欲望的犧牲品嗎?──是的,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現在平等權利被承認了。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中和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不得不廢除一切等級的即個人的特權,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後來逐漸在公法方面實施了個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從那時以來并且由於那個緣故,平等權利在口頭上是被承認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衹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觀念上的權利來滿足,絕大部分卻要靠物質的手段來實現,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所關心的,是使絕大多數權利平等的人僅有最必需的東西來勉強維持生活,所以資本主義對多數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所給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隸制或農奴制所給予的多一些。至於說到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況是否好一些呢?就連“薩多瓦的教師“不也是一個神話人物嗎?
不僅如此。根据費爾巴哈的道德論,証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衹要人們的投机始終都是得當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進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裡又善於正确地估量我的行為的後果,因而這些後果衹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損失,就是說,如果我經常賺錢的話,那麼費爾巴哈的指示就算執行了。我也并沒有因此就妨礙另一個人的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為另一個人和我一樣,是自愿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時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樣。如果他賠了錢,那麼這就証明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因為他盤算錯了,而且,我在對他執行應得的懲罰時,甚至可以擺出現代鵑達曼的威風來。衹要愛不純粹是溫情的空話,交易所也是由愛統治的,因為每個人都靠別人來滿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這就是愛應當做的事情,愛也在這裡得到實現。如果我在那裡正确地預見到我的行動的後果,因而賭贏了,那麼我就執行了費爾巴哈道德的一切最嚴格的要求,而且還成了富翁。換句話說,費爾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管他自己多麼不愿意或想不到是這樣。
可是愛啊!──真的,在費爾巴哈那裡,愛隨時隨地都是一個創造奇跡的神,可以幫助克服實際生活中的一切困難,──而且這是在一個分裂為利益直接對立的階級的社會裡。這樣一來,他的哲學中的最後一點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衹是一個老調子:彼此相愛吧!不分性別、不分等級地互相擁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簡單扼要地說,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和它的一切前驅者一樣的。它是為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衹要它能破壞這種道德而不受懲罰,它就加以破壞。而本應把一切人都聯合起來的愛、則表現在戰爭、爭吵、訴訟、家庭糾紛、离婚以及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盡可能的剝削中。
但是,費爾巴哈所提供的強大推動力怎麼能對他本人毫無結果呢?理由很簡單,因為費爾巴哈不能找到從他自己所极端憎惡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他緊緊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裡,自然界和人都衹是空話。無論關於現實的自然界或關於現實的人,他都不能對我們說出任何确定的東西。但是,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考察。而費爾巴哈反對這樣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對他來說衹意味著和現實世界最後分离,意味著退入孤寂的生活。在這方面,主要又要歸咎於德國的狀況,這種狀況使他落得這種悲慘的結局。
但是,費爾巴哈沒有走的一步,必定會有人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開始的。
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就他們沒有离開哲學這塊土地來說,都是黑格爾哲學的分支。旋特勞斯寫了《耶穌傳》和《教義學》以後,就衹從事寫作勒南式的哲學和教會史的美文學作品﹔鮑威爾衹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雖然他在這裡所做的也是重要的﹔施蒂納甚至在巴枯寧把他同蒲魯東混合起來并且把這個混合物命名為“無政府主義”以後,依然是一個怪物﹔唯有費爾巴哈是個杰出的哲學家。但是,不僅哲學這一似乎凌駕於一切專門科學之上并把它們包羅在內的科學的科學,對他來說,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義者,上半截是唯心主義者﹔他沒有批判地克服黑格爾,而是簡單地把黑格爾當作無用的東西拋在一邊,同時,與黑格爾体系的百科全書式的丰富內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矯揉造作的愛的宗教和貧乏無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麼積极的東西。
但是,從黑格爾學派的解体過程中還產生了另一個派別,唯一的真正結出果實的派別。這個派別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3]
同黑格爾哲學的分離,在這裡也是由於返回到唯物主義觀點而發生的。這就是說,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心毫不怜惜地拋棄一切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系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系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義并沒有別的意義。不過在這裡第一次對唯物主義世界觀采取了真正嚴肅的態度,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裡去了。
黑格爾不是簡單地被放在一邊,恰恰相反,上面所闡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辯証方法被接過來了。但是這種方法在黑格爾的形式中是無用的。在黑格爾那裡,辯証法是概念的自我發展。絕對概念不僅是從來就存在的(不知在哪裡?),而且是整個現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靈魂。它通過在《邏輯學》中詳細探討過的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預備階段而向自身發展﹔然後它使自己“外化”,轉化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沒有意識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經過新的發展,最後在人身上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在歷史中又從粗糙的形式中掙脫出來,直到絕對概念終於在黑格爾哲學中又完全地達到自身為止。因此,在自然界和歷史中所顯露出來的辯証的發展,即經過一切迂回曲折和暫時退步而由低級到高級的前進運動的因果聯系,在黑格爾那裡,衹是概念的自己運動的甸版,而這種概念的自己運動是從來就有的(不知在什麼地方),但無論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維的人腦為轉移的。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顛倒是應該消除的。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作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作絕對概念的某一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証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這樣,概念的辯証法本身就變成衹是現實世界的辯証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証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宁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我們發現了這個多年來已成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主義辯証法,而且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它。[4]
而這樣一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時也擺脫了那些曾經在黑格爾那裡阻礙它貫徹到底的唯心主義裝飾。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過程的集合体,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從黑格爾以來,已經成了一般人的意識,以致它在這種一般形式中未必會遭到反對了。但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實際上把這個思想分別運用於每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們在研究工作中始終從這個觀點出發,那麼關於最終解決和永恆真理的要求就永遠不會提出了﹔人們就始終會意識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識到他們在獲得知識時所處的環境對這些知識的制約性﹔人們對於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同一和差別、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也不再敬畏了﹔人們知道,這些對立衹有相對的意義,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認識都有它隱蔽著的、以後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今天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認識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從前才能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裡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作一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它的殘余還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方法在當時是有重大的歷史根据的。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一個事物是什麼,爾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樣。認為事物是既成的東西的舊形而上學,是從那種把非生物和生物當作既成事物來研究的自然科學中產生的。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也就響起了舊形而上學的喪鐘。事實上,直到上一世紀末,自然科學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學,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但是在本世紀,自然科學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是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聯系──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大的整体──的科學。研究植物机体和動物机体中的過程的生理學,研究單個机体從胚胎到成熟的發育過程的胚胎學,研究地殼逐漸形成過程的地質學,所有這些科學都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產兒。
但是,首先是三大發現使我們對自然過程的相互聯系的認識大踏步地前進了:第一是發現了細胞,發現細胞是這樣一種單位,整個植物体和動物体都是從它的繁殖和分化中發育起來的。這一發現,不僅使我們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個共同規律發育和生長的,而且使我們通過細胞的變异能力看出有机体能改變自己的物種從而能完成比個体發育更高的發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轉化,它向我們表明了一切首先在無机界中起作用的所謂力,即机械力及其補充,所謂位能、熱、輻射(光或輻射熱)、電、磁、化學能,都是普遍運動的各種表現形式,這些運動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關系由一種轉變為另一種,因此,當一種形式的量消失時,就有另一種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現,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運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不斷轉化的過程。──最後,達爾文第一次從聯系中証明,今天存在於我們周圍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內,都是少數原始單細胞胚胎的長期發育過程的產物,而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過化學途徑產生的原生質或蛋白質形成的。
由於這三大發現和自然科學的其他巨大進步,我們現在不僅能夠說明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系,而且總的說來也能說明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系了,這樣,我們就能夠依靠經驗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歸。描繪這樣一幅總的圖歸,在以前是所謂自然哲學的任務。而自然哲學衹能這樣來描繪:用觀念的、幻想的聯系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系,用想象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臆想來填補現實的空白。它在這樣做的時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預測到一些後來的發現,但是也發表了十分荒唐的見解,這在當時是不可能不這樣的。今天,當人們對自然研究的結果衹要辯証地即從它們自身的聯系進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令人滿意的“自然体系”的時候,當這種聯系的辯証性質,甚至違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們受過形而上學訓練的頭腦不得不承認的時候,自然哲學就最終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圖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
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适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适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在這裡,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系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証實的現實的聯系,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作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衹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裡,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歷史事變中的內在聯系。這樣,人們就用一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祕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系。因此,在這裡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裡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
但是,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証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因為在這一領域內,盡管各個人都有自覺預期的目的,總的說來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著。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很少如愿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扰,彼此沖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這樣,無數的單個愿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後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這樣,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衹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
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因此,問題也在於,這許多單個的人所預期的是什麼。愿望是由激情或思慮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激情或思慮的杠桿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動机,如功名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愿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机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衹有從屬的意義。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机背後隱藏著的又是什麼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机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麼?
舊唯物主義從來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因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机來判斷一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拈者,而小人是得胜者。舊唯物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歷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東西﹔而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後面的是什麼,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麼。不徹底的地方并不在於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於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相反,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所代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机和真實動机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机後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但是它不在歷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反而從外面,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動力輸入歷史。例如黑格爾,他不從古希腊歷史本身的內在聯系去說明古希腊的歷史,而衹是簡單地斷言,古希腊的歷史無非是“美好的個性形式”的制定,是“藝朮作品”本身的實現。在這裡,黑格爾關於古希腊人作了許多精彩而深刻的論述,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今天對那些純屬空談的說明表示不滿。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机背後并且构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麼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机,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机﹔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机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但是這一切在人們的頭腦中采取什麼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情況決定的。現在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萊茵地區那樣簡單地搗毀机器,但是,這決不是說,他們已經容忍按照資本主義方式應用机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個時期,對歷史的這些動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系是混亂而隱蔽的,在我們今天這個時期,這種聯系已經簡化了,以致人們有可能揭開這個謎了。從采用大工業以來,就是說,至少從1815年簽訂歐洲和約以來,在英國,誰都知道,土地貴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資產階級(middle class)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是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法國,隨著波旁王室的返國,同樣的事實也被人們意識到了﹔复辟時期的歷史編纂學家,從梯葉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總是指出這一事實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而從1830年起,在這兩個國家裡,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被承認是為爭奪統治而鬥爭的第三個戰士。當時關系已經非常簡化,衹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這三大階級的鬥爭和它們的利益沖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的動力。
但是,這些階級是怎樣產生的呢?初看起來,那種大的、曾經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的起源,還可以(至少首先)歸於政治原因,歸於暴力掠奪,但是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就說不通了。在這裡,顯而易見,這兩大階級的起源和發展是由於純粹經濟的原因。而同樣明顯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一樣,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是由於經濟關系發生變化,确切些說,是由於生產方式發生變化而產生的。最初是從行會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的過渡,隨後又是從工場手工業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業的過渡,使這兩個階級發展起來了。在一定階段上,資產階級推動的新的生產力──首先是分工和許多局部工人在一個綜合性手工工場裡的聯合──以及通過生產力發展起來的交換條件和交換需要,同現存的、歷史上繼承下來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產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說,同封建社會制度的行會特權以及許多其他的個人特權和地方特權(這些特權對於非特權等級來說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資產階級所代表的生產力起來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會師傅所代表的生產秩序了﹔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國是逐漸打碎的,在法國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國還沒有完全打碎。但是,正像工場手工業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曾經同封建的生產秩序發生沖突一樣,大工業現在已經同代替封建生產秩序的資產階級生產秩序相沖突了。被這種秩序、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範圍所束縛的大工業,一方面使全体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沒有銷路的產品。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証明,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裡,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志的動机,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一個階級統治著),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一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一內容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优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一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麼,以前的一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丰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著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衹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麼,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一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一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衹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最充分地証實這一點﹔但是,在這裡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如果說國家和公法是由經濟關系決定的,那麼不言而喻,私法也是這樣,因為私法本質上衹是确認單個人之間的現存的、在一定情況下是正常的經濟關系。但是,這種确認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們可以把舊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來,并且賦予這種形式以資產階級的內容,甚至直接給封建的名稱加上資產階級的含義,就像在英國與民族的全部發展相一致而發生的那樣﹔但是人們也可以像在西歐大陸上那樣,把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即羅馬法以及它對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的關系(如買主和賣主、債權人和債務人、契約、債務等等)所作的無比明确的規定作為基礎。這樣做時,為了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半封建的社會的利益,人們可以或者是簡單地通過審判的實踐貶低羅馬法,使它适合於這個社會的狀況(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謂開明的進行道德說教的法學家的幫助把它加工成一種适應於這種社會狀況的特殊法典,這種法典,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從法學觀點看來也是不好的(普魯士邦法)﹔但是這樣做時,人們也可以在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後,以同一個羅馬法為基礎,制定出像法蘭西民法典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因此,如果說民法准則衹是以法的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那麼這種准則就可以依情況的不同而把這些條件有時表現得好,有時表現得壞。
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一個机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机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一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机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一階級的統治,它就越獨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必然要變成政治的鬥爭,變成首先是反對這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爭﹔對這一政治鬥爭同它的經濟基礎的聯系的認識,就日益模糊起來,并且會完全消失。即使在鬥爭參加者那裡情況不完全是這樣,但是在歷史編纂學家那裡差不多總是這樣的。在關於羅馬共和國內部鬥爭的古代史料中,衹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訴我們,這一鬥爭歸根到底是為什麼進行的,即為土地所有權進行的。
但是,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產生了另外的意識形態。這就是說,在職業政治家那裡,在公法理論家和私法法學家那裡,同經濟事實的聯系就完全消失了。因為經濟事實要以法律的形式獲得确認,必須在每一個別場合都采取法律動机的形式,而且,因為在這裡,不言而喻地要考慮到現行的整個法的体系,所以,現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經濟內容則什麼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兩個獨立的領域,它們各有自己的獨立的歷史發展,它們本身都可以系統地加以說明,并需要通過徹底根除一切內部矛盾來作出這種說明。
更高的即更遠离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采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裡,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系,越來越錯綜复雜,越來越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系是存在著的。從15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复興時期,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同樣,從那時起重新覺醒的哲學也是如此。哲學的內容本質上僅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适應的思想的哲學表現。在上一世紀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經濟學家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那裡,這種情形是表現得很明顯的,而在黑格爾學派那裡,這一情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
現在我們再簡略地談談宗教,因為宗教离開物質生活最遠,而且好像是同物質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於他們本身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界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但是,任何意識形態一經產生,就同現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并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識形態了,就是說,它就不是把思想當作獨立地發展的、僅僅服從自身規律的獨立存在的東西來對待了。人們頭腦中發生的這一思想過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這一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了。因此,大部分是每個有親屬關系的民族集團所共有的這些原始的宗教觀念,在這些集團分裂以後,便在每個民族那裡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條件而獨特地發展起來,而這一過程對一系列民族集團來說,特別是對雅利安人(所謂印歐人)來說,已由比較神話學詳細地証實了。這樣在每一個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這些神的王國不越出它們所守護的民族領域,在這個界線以外,就無可爭辯地由別的神統治了。衹要這些民族存在,這些神也就繼續活在人們的觀念中﹔這些民族沒落了,這些神也就隨著滅亡。羅馬世界帝國使得古老的民族沒落了(關於羅馬世界帝國產生的經濟條件,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滅亡了,甚至羅馬的那些僅僅适合於羅馬城這個狹小圈子的神也滅亡了﹔羅馬曾企圖除本地的神以外還承認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種世界宗教來充實世界帝國的需要。但是一種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這樣用皇帝的敕令創造出來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經從普遍化了的東方神學,特別是猶太神學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學,特別是斯多亞派哲學的混合中悄悄地產生了。我們必須重新進行艱苦的研究,才能夠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麼樣子,因為它那流傳到我們今天的官方形式僅僅是尼西亞宗教會原為了使它成為國教而賦予它的那種形式。它在250年後已經變成國教這一事實,足以証明它是适應時勢的宗教。在中世紀,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基督教成為一種同它相适應的、具有相應的封建等級制的宗教。當市民階級興起的時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國南部的阿爾比派中間,在那裡的城市最繁榮的時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對抗而發展起來。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并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采取神學的形式﹔對於完全由宗教培育起來的群眾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市民階級從最初起就給自己制造了一種由無財產的、不屬於任何公認的等級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種仆役所組成的附屬品,即後來的無產階級的前身,同樣,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兩派:市民溫和派和甚至也為市民异教徒所憎惡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絕是同正在興起的市民階級的不可戰胜相适應的﹔當這個市民階級已經充分強大的時候,他們從前同封建貴族進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鬥爭便開始采取全國性的規模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行動發生在德國,這就是所謂的宗教改革。那時市民階級既不夠強大又不夠發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級──城市平民、下級貴族和鄉村農民──聯合在自己的旗幟之下。貴族首先被擊敗﹔農民舉行了起義,形成了這次整個革命運動的頂點﹔城市背棄了農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軍隊鎮壓下去了,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實。從那時起,德國有整整三個世紀從那些能獨立地干預歷史的國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國人路德外,還出現了法國人加爾文,他以真正法國式的尖銳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使教會共和化和民主化。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并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党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并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在這裡,加爾文教顯示出它是當時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於一部分貴族同資產階級間的妥協而結束以後,它也沒有得到完全的承認。英國的國教會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國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強烈地加爾文教化了。舊的國教會慶祝歡樂的天主教禮拜日,反對枯燥的加爾文派禮拜日。新的資產階級化的國教會,則采用後一種禮拜日,這種禮拜日至今還在裝飾著英國。
在法國,1685年加爾文教的少數派曾遭到鎮壓,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驅逐出境。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那時自由思想家皮埃爾﹒培爾已經在忙於從事活動,而1694年伏爾泰也誕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衹是使法國的資產階級更便於以唯一同已經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相适應的、非宗教的、純粹政治的形式進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國民原會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見,基督教進入了它的最後階段。此後,它已不能成為任何進步階級的意向的意識形態外衣了﹔它越來越變成統治階級專有的東西,統治階級衹把它當作使下層階級就範的統治手段。同時,每個不同的階級都利用它自己認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穌會派或新教的正統派,自由的和激進的資產者則利用理性主義,至於這些先生們自己相信還是不相信他們各自的宗教,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這樣,我們看到,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系即經濟關系引起的。在這裡衹說這一點就夠了。
上面的敘述衹能是對馬克思的歷史觀的一個概述,至多還加了一些例証。証明衹能由歷史本身提供﹔而在這裡我可以說,在其他著作中証明已經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証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現在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不再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聯系了。這樣,對於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麼的話,那就衹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於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証法。
隨著1848年革命而來的是,“有教養的”德國拋棄了理論,轉入了實踐的領域。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小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已經為真正的大工業所代替﹔德國重新出現在世界市場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國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割据、封建殘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礙這一發展的最顯著的弊病。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開哲學家的書房而在証券交易所築起自己的殿堂,有教養的德國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國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時代曾經是德國的光榮的偉大理論興趣──那種不管所得成果在實踐上是否能實現,不管它是否違反警章都照樣致力於純粹科學研究的興趣。誠然,德國的官方自然科學,特別是在專門研究的領域中仍然保持著時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國《科學》雜志已經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單個事實之間的重大聯系方面的決定性進步,即把這些聯系概括為規律,現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國,而不像從前那樣出在德國。而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衷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這種科學的官方代表都變成毫無掩飾的資產階級的和現存國家的玄想家,但這已經是在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同工人階級公開敵對的時代了。
德國人的理論興趣,衹是在工人階級中還沒有衰退,繼續存在著。在這裡,它是根除不了的。在這裡,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相反,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并且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它在官方科學那裡是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
寫於1886年初
原文是德文
載於1886年《新時代》雜志第4期和第5期,並於1888年以單行本形式在斯圖加特出版
[1]哲學博士卡.尼.施達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85年斯圖加特版,恩克書店版。
[2]在蒙昧人和低級野蠻人中間,現在還流行著這樣一種觀念:夢中出現的人的形象是暫時離開肉體的靈魂;因而現實的人應當對自己出現於他人夢中時針對作夢者而採取的行為負責。例如伊姆.特恩於1884年在圭亞那的印地安人中就發現了這種情形。
[3]請允許我在這裡作一點個人的說明。近來人們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參加了制定這一理論的工作,因此,我在這裡不得不說幾句話,把這個問題澄清。我不能否認,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這以前和在這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但是,絕大部份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後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於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幾個專門的領域外,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於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